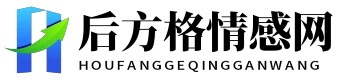黄浦江畔的宁静饭店,曾经是上海最豪华的地方,她如同一位踏着高跟鞋的女人,在1937年的水边站立。现在,当我们再次走进她的怀抱,她已经老去。时间流转,我们来到了那个现在,那个充满假定的现在。

宁静饭店,是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一座哥特式建筑,它是外滩上最早兴建的大楼。在远东战前的时光里,有些老日本人还会提起她,他们闭上眼睛,就像回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一样。那座楼上的长廊安静而温暖,被青铜壁灯照亮。在那里,一些三四十年代的人物会出现,如恩雅和岑寂。
他们穿着前面有一根抹筋的玻璃丝带,男人抽着时髦的埃及香烟。吴宇森拍摄的小说《宁静饭店》讲述了一个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,那个时代没有,但那个时代总能例外,让我喜欢他们爱欲哀愁眼中的泪水。

岑寂后来死在上海,他永远躺在虹桥的一个墓地里,与其他从法国归来的老朋友相伴。他生前总想自己是个法国人,现在他终于满足了,只是他的墓碑用的是普通石料,名字刻得很简朴——玄色刻制。他毕竟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。
你要路过,我要暂停

恩雅说:我现在走在东山的小巷里常常会反思一生,而也许我的一生就像这一条小巷,暗淡如旧路灯、暗淡如旧光线,人走在里面,就像是剪纸贴在墙上。但它却很自然,小巷有新鲜之处,不管它多新多晚,它很快就会变成古老,就象我眉间鱼尾纹。但是我依然喜欢慢慢地走过去,就像留声机上的那张老唱片,无需通知你,那个留声机是束缚后的东西,也是上海出产的,看似粗糙但耐用。
小巷尽头,有一张竹椅。一位老人坐在竹椅上,对面的屋檐下面有光芒停留。她半睁半闭眼睛,说着私房话给小巷听。小巷或许听,或许不再听,或许只是如此。

岑寂看着咖啡馆外面的世界,一位小姐突然走过来。她推荐“盐汽水”,穿着齐膝改良旗袍、短开丝米毛衣、一头短发。她看着岑寂不置可否,因为他明天带来了上海小开三件宝——怀表、皮带、皮夹子。而小姐的话语多么无聊,却因为这些理由而流露出好奇心和期待心。
世界上谁不知道上海?这是欧洲人当年挂出来的一句横幅。不过现在我们只看到旧房子的烟囱竖立着,有法国式也有英国式。黄浦江快速地带走了尘土上的故事,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,都忘记了珍惜那些情感共鸣的小事儿。我站在江边,一双雪白的手套包裹了一封信,而我的口袋里还有两张去香港船票,现在什么都不值钱,只除非黄金和美圆。我自从留学返来就在英资银行工作,也就是那时候认识恩雅的。

1914年洋泾滨填海成了爱德加街,我们却熟视无睹;第一家跑马场正式营业,比如美国来的剧作家整天躲在永远拉白色丝窗帘房间写下关于上海;比如几年后外国人的《大饭店》电影里的故事。这是一个英派青年,这是一个罗敷有夫女职员背景下的故事。当时,他们通过信件交流,每封信都是他们彼此生活点滴所分享的事务,比如尝试骑马尝试饮酒等日常琐事,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与担忧。
1992年宁静饭店被国际知名酒店组织评为全球最著名酒店之一。恩雅作为最后几位活跃于该餐厅工作人员之一,她收到了观礼邀请函,当这份邀请函传到她手中的时候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,可有人记取自己也是件开心的事,她哭了一整晚,因为她知道自己白发苍苍流泪模样不好看,但如果岑寂想到未来自己会这样,还会不会每日寄去没有落款的情书呢?
我要暂停,我要路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