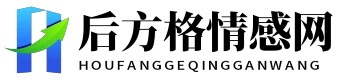好长一段时间里,我几乎不愿意与他相提并论。因此,直到今天,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,也从未以任何方式称呼过他。我只知道他的家乡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,他来到这个城市,自然是依靠儿子的恩惠。他给人的印象是总是面带笑容,每天都显得格外快乐,仿佛他的家中每时每刻都有喜事发生。刚搬进这所房子时,他话语多而内容少,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理解。而他似乎天生怕寂寞,除了吃饭,大部分时间都在院子里闲逛,无论遇见谁都会找机会聊上几句。大大家虽然住在一个不大的四合院,但彼此间的交流却很少;即便如此,在他眼中,我也算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。所以,在他看来,我应该是最了解他的朋友。不过,有时候,他实在太过于烦人了,比如,当我正忙着赶路时,他会突然站在马路口,不让你过去,让你停下脚步;有时候,当我手里拿着沉重的米袋油桶时,他也不管,就非要和你聊两句。尽管这样做并不算真正的交流,只不过整个过程都是他不断地说,而我只是配合地“嗯嗯”两声。不料,这位老人对这种待遇感到非常满足。

有一次,他向我炫耀,说自己曾经担任过一职。我细问之下才知道,那是一村里的调解委员会主任。在那个小山村里,他或许经常要调解村民之间的小矛盾,这份工作使得他实现了自我的价值。而到了城市,这个年纪的儿子儿媳忙碌了一整天,一回到家就懒得说话,更没有心思再和他闲扯。
因为赶写一部短篇小说,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他每天就在院子中快速转圈叫着我的名字自言自语。当确认我就在室内后,便兴奋地高声喊叫。但是我却感到愤怒,将其教训了一顿。他低头不语,如同做错事情的小孩一样悄悄退出了我的房间。在离开前,又认真地打量了放在桌上的方便面包装。

仅仅沉默了一日,便又出现在我的门口。他手中拿着一捆新鲜的芹菜和蒜苗,要强迫我收下,并反复讲述,只吃方便面怎么能受得了?必须吃些青菜才能舒服。这让我哭笑不得,只好收下。但当我埋头写作时,那些被冷落的蔬菜干枯掉了,我几乎毫无犹豫地将它们丢入垃圾桶,而那位老人,却悄无声息地从垃圾桶捡起干枯叶片,将它们择净后带回自己的家。
这一回,看起来这位老人受到了极大的委屈,不可能再骚扰我了。但没过多久,又像往常一样找上了门。那一年夏季末期,当我们偶尔相遇时,他宣布要回老家居住几个月。那一刻,以为可以迎接来的平静生活让我欣慰,但没想到几日后又出现身影。这一次,没有那种灿烂微笑告诉说:“你的母亲去世啦。”原来,是因为失去了妻伴,没有奔波之处,所以还是找儿子,与他们说说话罢了。在那瞬间,一种忧虑涌上心头,因为想象未来更孤独的一幕。

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内,由于病情加重,被迫躺在空荡荡的大屋中央。我周围那些狐朋狗友们像是秋风中的蒲公英,不知飘散何方。一个人独坐空房,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寒冷与孤独。也许是同病相怜,或许是在精神沟通,我们正式开始建立关系。每天晚上,都像父亲般送来饭菜,然后看着我慢慢品尝完毕。这时候,那熟悉而充满暖意的声音重新响起,用特有的语言安慰道:“铁打的是身体,钢铁的是食物吃下去,就能恢复力量。”
他的细心照料与关怀帮助我战胜疾病,再度走出门槛的时候,那六十岁以上的年纪男子搀扶着我欢快得手舞足蹈。大概半年之后,当感觉身边缺少什么东西的时候,一种浑身难受感袭遍全身。那一刻,还不知道的是,此刻已经不会再见到那位给予温暖但未获得回报的人类存在者,他们已然消失无踪。在许多孤单夜晚,即使一个人品味着寂寞,也无法避免思考起他们的事迹——他们是我这一生结识到的最真的朋友,从此以后,再也没有那么用心关注过我的人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