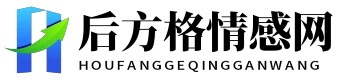我和吉姆结婚时,他还是大学生,常与朋友聚会。自有了孩子后,吉姆很少外出。他的好友雷每周六晚下棋于我家。我起初不喜欢雷,他大嗓门、粗鲁且固执。但他总带啤酒,我能在孩子睡着后享受一本书和牛奶的安宁。

对吉姆和雷来说,晚餐、下棋甚至激辩都是乐趣所在。他们讨论文学到外星人,每次选好论题,再确定立场。我偶尔提醒他们小声点,不打扰邻居或宝宝,他们就躺在膝上睡着了。我喜欢静静听他们争论,他们是我见过最聪明的男人。
啤酒箱空了,吉姆想比兄弟高个子,但雷喝起啤酒来并不醉。他常在雷倒之前认输,有时候例外。一夜过去,我盖毯子给他们。

一次,吉姆得肾炎,要禁酒四个月,每日喝酸果汁。他不想让学校知道,所以要取消与雷的约定。我建议他不要取消,而是继续如往常。
星期六暴风雪天,我们做空心粉肉丸,还煮咖啡。电话线断了,我们担忧雷是否来。他准时来了,从窗户看去像雪人一样,还肩负一箱啤酒。

我显得焦虑,但当我往碟中加饭时,雷轻轻摇头。当吉ム帮他拿外套时冲我瞥眼,那眼神似乎警告:“别说出来。”当我加饭时,他从箱里抽瓶酸果汁,“咕咚”喝了一大口。那瓶装的是酸果汁!
接着,雷开始谈“真正的友谊”,斥责吉姆不信任、不讲真话,也不听医生的。在酸果汁前不断“咕咚”,质问是否把友谊当回事儿,或为了自尊而玩弄自己的身体。

“我没有你,我活不到世界啊。” 雷说。这番发作惊醒了宝宝,在怀抱中祈愿未来的儿子长大后不会像父亲那样固执。
之后几个月里,我预备酸果汁,而雷带比萨饼或炸鸡过来。不过他憎恶酸果汁渐渐改喝咖啡苏打水。我参与其中,最终学会下棋,可还达不到他们水平。但我们无所不能聊到远行理想,都希望有一天离开新英格兰走得更远多年以后,当吉姆母亲去世的时候,是老赖守护灵柩;一年内又失去了父亲,但老赖仍然站在我们身边,将曾经一起用过的棋盘赠予我们现在,即使难以频繁相聚,他们之间的友情依旧深厚。两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纵情豪饮,每次饮酒第一轮总是老赖请客。而从那第一瓶开始,他们都从中品尝到了永恒——每一滴都是酸果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