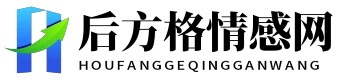学校有个第二文化,我称之为非学术文化,这类东西是与生俱来的,从你进入学校开始你就具备或拥有的资产和能力,野名字,也就是错号,就如同你爹妈生你的时候给你取得大名一样。它会跟随者你一辈子,除非你很不喜欢你的野名字,然后你努力寻找一个洞想把自己藏起来,等大家都忘记了你不喜欢的那个野名字然后抛头露面,后来发现,大家还是这么叫你。这就是野名字。 很有趣的是80后的野名字都很朴实,而且各种模仿。我从来没觉得野名字是对人的侮辱,我觉得是你唯一记得的儿时的一种标记,是帮助你记忆起一些有趣的事儿和值得怀念的人的狠好的载体。 小时候,每个班里面总有一两个神仙,只要哪儿来个新同学,必然给它取个野名字,而且这个名字肯定不是在外貌、性格、籍贯或者在其他习惯、特长等等或者发生一件很出奇的事件,反正是挂钩的、相符的,而且越叫越相符。我觉得这几个神仙特别有才,真的,不去当个算挂的郎中,真的可惜。记忆中,我的小学同学董帅就是八路神仙中的一路,自然他给自己取的要高尚点,就叫帅帅,虽然认识越长越丑了,没有小学时候那个虎头虎脑的娃可爱,但是人毕竟是帅帅,去年我表姐结婚,我们酒桌上,我还是很腻歪的称其为帅帅,包括一桌的济公,裁缝机,还有阿迷晒。济公是我四年级很要好的兄弟,但是五年级分班之后各立门户,但是这还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友谊,真的不错。不过我觉得我错了,升高学后,升大学后,都没有和这些人有密切的联系和接触,是我疏远了他们。真应该在念完书后,慢慢地捡回本应该一如既往的东西。我记得济公到我们村里玩,光着在我们村的河里面玩水,然后我带着他偷甘蔗,然后第二天被某某举报被班主任罚站黑板,刚好那天天热,济公觉得被人举报很不爽,但是也没办法,因为举报我们的是个女同学,济公只能跑到学校水龙头用水冲了下头,解解火气,然后没有干毛巾,用手把头发往中间一缕,和那会儿很热播的电视剧《济公》里的角色有的一拼,然后刚刚好神仙看见了,赐予之济公一名。我记得坐我前面的裁缝机比较有意思,她现在不做央视名嘴真的可惜了、浪费了。只有我在后面做出一些让她有点小不爽的事情,那么,接下来将是我无法学习的一顿话,我几乎每天都能享受到,但是,我也听不懂你叽里呱啦的一堆说的是什么,勉强有一天她安静地坐着,我倒是有些不习惯。碰到我耐心这么好的男人,真是福气,但是她偏偏某天碰上了神仙,神仙就很贴切的形容她那种讲话的风格和语速和那种重复频率,如果是你你想得出裁缝机这个事物么,太尼玛逼真了。以至于后来每次听她讲话,我都感觉自己面前是一台机器。如果恰逢裤子开裆了,被她这么一折腾,立马给“缝”好了。这就是裁缝机。 小学生的错号是有规律和章法的,大概出于同一个祖师爷的缘故,至少80年代的人这样。如果你姓周,那么你必然叫周扒皮,就像我姓黄,那么我必然就是大黄,小时候大人就会叫我小黄,可能再过30年就有人叫我老黄一样,如果你头很大,那么你必然是大头或者猪头,如果你很胖,那么你就是胖子或者肥仔,如果你长的很黑,那么你叫乌皮或者初中上过地理课后一哥们得了个***的外号,牛的一米,前几天听说有同学结婚了,一问是谁,答***。类似外形、相貌、姓名等,由来名字之处比比皆是,比如你是江西来的,我们这儿的人就称你为赣西老表,这是定律、是不变的真理,我的小学有一个老表同学,初中也有一个老表同学,但是,他们都落叶归根了。 你有没有感觉到,很多你的同学已经很陌生了,这是一件很凄凉的事情,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我觉得我往北去读书是一个失误,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失误,每次北上一点,就感觉丢到几个伙伴,但是,失去一斤友谊的瞬间,又得到另一斤友谊,人这一辈子得得失失,真的无法计算。什么是得到,什么又是失去。依稀记得的还是那些可爱的野名字,就像路边的野花那样风雨吹打不烂,永远镌刻着属于它自己意义的那段光荣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