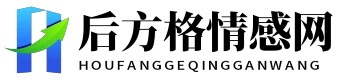每年一到腊月,母亲便催促着我回村过节。母命难违,只好丢下所有的琐事,携一家几口前去“复命”。 煮腊八粥的豆子、干果之类的都是母亲在秋天里准备的,用一个个陶罐仔细地封存,藏到一个隐秘的角落。到腊月初七的下午,母亲便拿出来剥壳、淘洗,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后辈参与。她那一双皲裂的手伸进这腊月的冰水里时,我的心便如刀扎一般,而母亲竟然高兴地哼起了小曲。自我有记忆时起,每年都如此。只是,那小曲在一年年苍老,一年年嘶哑。 腊八节这天,母亲一反常态地放纵我睡懒觉,下着雪的天气,我睡在热炕上的被窝里,舒服得不想动。但屋里炉子上腊八粥的香甜味,早已扰乱了我的梦。我从被窝里探出头,整个屋里已被蒸汽笼罩,窗户的玻璃也模糊成了半透明。母亲就坐在窗下纳鞋底,她身旁的簸箩里放着厚厚一沓红色的窗花。 母亲见我起来,赶紧放下手里的鞋底,有些吃力地站起来,从外面端进来一盘酸菜。她掀开门帘的瞬间,我看到的雪填满了帘与门之间的三角口子,进来的寒风把我的脸撞得生疼。孩子们在雪地里的打闹声,把时光撞得乱颤,抖落了枝头的喜鹊。 白雪覆盖的屋子里,我们一家人围炉而坐,幸福便在这一碗碗腊八粥的氤氲里升腾,任它窗外北风萧瑟、寒气凛冽,小屋里却是阳春三月、暖从心淌。腊八粥配酸菜,可谓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美味佳肴。每一口都能吃出这寒冬里最舒适的温暖,每一口都能体会到透彻心扉的宁静,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彻身激荡的感动。 母亲说过:“过了腊八,长一杈把。”以前并不懂此话深意,只能体会到词语押韵时碰撞出的语言快感。年岁渐长,方才明白,这是人们在面对时光悄无声息的流逝时,发出的无奈叹息。一天长过一天,一天暖过一天,时光一“杈把”一“杈把”划减着人生的余量。而人,你觉察也好,不察也罢,时光依然“逝者如斯”。古人的智慧无疑是伟大的、令人惊叹的,居然以“杈把”这种常见的农具,反向丈量着时光的长度,丈量着年的距离。 日子是不经数的,年是一天天近了。你看那几个顽皮的孩子,已经在张罗着贴窗花了。在这白雪覆盖的屋檐下,一团团火红的喜悦给空气裹上了年味,那沾了喜的雪花儿踮着脚,轻轻地把幸福洒满人间。